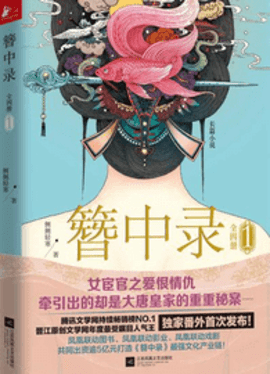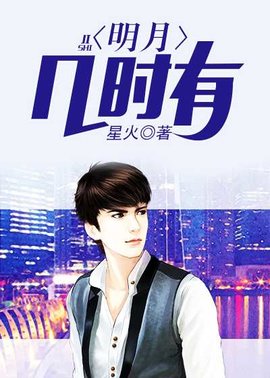《一别经年》这是一个发生在襄王二十年的故事。故事的第一个重要事件是徐孟丘被满门抄斩,导致全府上下千余口人被青龙兵屠杀。第二个事件是当朝皇帝驾崩,太子因悲伤而生病,四王殷王继位。然而,这些事件都发生在十三年前。在殷王十三年的统治下,政治稳定,社会繁荣。百姓夜不闭户,孩童皆有书可念,官吏清明,城中各种场所繁荣兴盛。故事的主要场景是燕城,其中若莱茶楼是一个重要的地方,每月七日白豫礼会在这里为人们义诊。虽然豫庄和礼馆以白豫礼的名字命名,但他并不是个富有的人。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身着浅青长衫的公子,他在若莱茶楼为人诊病。他用手指触摸来人的手腕,七个来回后,无论是大病还是小病,都能治愈。
一别经年小说精彩阅读:
襄王二十年有好几件大事,这排名第一的自然是家大业大的盐商徐孟丘一夜间被满门抄斩,全府上下千余口人被青龙兵就地屠杀。听说那晚的天是红色的,徐府霎时堪比人间炼狱,血水溢过门槛,刷洗几条长街。
同月,当朝皇帝驾崩,太子悲伤欲绝一病不起,四王殷王继位。这件事屈居第二,大概是改朝换代的风雷吹打了太久,百姓们都不耐烦了。不过,这都是十三年前的事儿了。
殷王十三年,政通人和。百姓夜不闭户,路不拾遗;孩童无论男女,皆有书可念;城中郡里,官吏大都清明,书馆、武场、戏院、茶楼沿街开遍了花儿,尽是一派繁荣景象。
若要来到这燕城,必要提及的定是这若莱茶楼了。
每月七日,城中城外享誉盛名的白豫礼白大夫都会在这若莱茶楼义诊。其实吧,每月这个日子来瞧病的人并不是很多,昌盛年月,谁有个不舒服都会毫不耽搁地朝豫庄、礼馆来回跑,富贵点儿的人家,更会把礼馆的大夫请回家来,大概只有那些个礼馆看不了的病才会等到七日这一天来白大夫这儿。
说到豫庄和礼馆,这当然是白豫礼的产业。在燕城,豫庄有三家,卖得是些常用的药材。礼馆有九家,也就是医馆。虽然是以白大夫的名字命名,但这白大夫却不是个财大气粗的主儿。
只见若莱茶楼厅堂北面的红楠木雕桌前坐着个身着浅青长衫的公子,他微微一点头,示意来人挽起衣袖把手腕放在垫枕上。来人约摸是个挑夫,此时搭在肩上的白里透着灰的汗巾还没卸下,粗壮的胳膊上也还溢着浑浊的汗。公子倒是不在意,仍是掀起他的蚕丝白绢儿盖在那人腕上,伸出三指搭了上去。
七,当人们呼吸了七个来回,白大夫就把病瞧好了,无论大病小病。用他的话说,七个喘息,对病人负责,我也有自信。
白豫礼撤下白绢儿,拿起一侧的纸笔写着药方,不紧不慢,再放下笔,双手托起方子递给那壮汉。整个若莱茶楼静得几乎要凝滞了空气,大家生怕粗喘了个气儿,就打破了白大夫脸上的一片静好。
和以往义诊的日子一样,若莱茶楼坐满了人,不知这喝茶的人里又有几个是单纯冲着看一眼“燕城三公子”之三的白豫礼来的。
“你看二楼廊间那位大臂上文着青蛇头的双刀大汉,大概就不是善类,约摸着也是......”红衣男子话还没说完,那大汉就从二楼一跃而下,就势劈开红楠木桌,立在白豫礼面前。
像是见惯了这场面,白大夫只看了眼大汉的脸,就再也没有把视线放在他身上。
“交出紫凝丹!饶你好死!”大汉拔刀,生怕自己声响不够大,引不了对面那人注意。
“络石。”同以往一样,出声的人头也没抬,大家只从白大夫的口中听到过这两个字,不紧不慢。
名唤络石的是个结实的青年,也是一袭浅青色衣衫,袖口裤脚都扎得紧实,一看便是习武之人。是啊,这么抛头露面又传闻拥有解百毒的紫凝丹的人怎么会没个护卫。只见络石拔剑,没有漂亮的剑花,干净利落,剑起剑落间,文身大汉已轰然倒地。
这儿的茶客们也是悠闲地喝茶,看戏一般。这样的场景每月都有,已经见怪不怪了。只是那络石,怕是免不了又要去官府走一遭,解释一通了。
“主子,今日就这样吧。”
见已没有了什么来人,白豫礼似有若无地“嗯”了声,朝门口走去。
“慢着!”
白豫礼顿了顿脚步,没有回头。他也很好奇自己为什么会为这傲慢无礼的两个字停下,皱了皱眉,怕是最近忙得紧了吧。回了回神,继续迈开脚步。
“哎呦,我说,等等我呀。”,一个红色身影从二楼廊间飞下,两三步间就挪到白豫礼眼前,“我我我,就是我呀。”
络石谨慎地挡在他主子身前,打量起眼前人来,“你有何事?”
红衣男子嘻嘻一笑,“嘿,看病呀。我这病还没瞧呢,你家主子怎么就走了呀。”说着,又把脸往白豫礼眼前凑了一凑。
络石轻瞥,“公子,我看您面色红润,气色不差,还能飞上飞下,敢问您哪儿病了?”
“心啊!心病哟...诶...”,红衣男子做捧心状,一脸惋惜的样子,“你说说,我这么个风流倜傥的绝世男子怎么就得了心病了呢,真是天妒英才...可惜啦...”
红衣男子还在叨叨地说着,白豫礼这才抬眼看他。面相正常,说是有病,确实牵强了,只是...那眸子...倒是有些迷惑人的味道。许是这双眼生得太好,白豫礼又多看了这脸一番,五官精致,线条柔和,比不上落雁美人的阴柔,但也没有七尺男儿的刚毅。各处都长得恰到好处,说是美男子也不为过。可...瞧着就是有些怪。
回了回神,白豫礼踏出了若莱茶楼大门,管他美男子嘁嘁喳喳,再也没回头了。
白豫礼在这燕城的宅子和若莱茶楼只隔着一条街,穿过一个小巷子便是。巷道里总有六七岁的孩童在自家门口堆石头,每每看到这,白豫礼风平浪静的脸才会有一丝变化。
“主子,要去调查那人吗?”
“嗯?”白豫礼正看着两个小孩比赛堆石子,没回过神。
“那个红衣公子瞧着倒不像是坏人,但我们刚稳住根基,不能有一丝意外。您说他这人也是奇怪,看病吧不像病人,打劫吧人家也根本没提那紫凝丹,尽是一个劲儿地夸自己好,哪有这样的人啊,不过那人长得也确实是好,您说......”

“怎的?今天这么多话?”白豫礼打断他。那个赤脚的小孩儿赢了。知道取舍,放弃了不平整的大石头,慢慢堆着小石头,在旁边那人竭力维持平衡时,他就赢了。白豫礼有些满意,又补了句,“怕不是看上人家了?”
络石这个大汉怎禁得这般调戏,脸咻地红了,忙开口解释,“我...我...怎么......”
“是谁看上我啦?”
熟悉地、戏谑地声音从身后传来,白豫礼也好奇自己为何有些期待地转过身,虽是脸上平静如寒潭,但心中却噔地一下,“果然是他。”